10世紀以后,中國印刷術的主流是木刻印刷,到19世紀依然如此;而西方自15世紀開始印刷直到19世紀,都以活字印刷為主流。西方活字印刷術的三個要素是:鑄造的金屬活字、垂直壓印的印刷機和油性墨;相對于此,中國木刻印刷的要素則是手工雕板、水平刷印的刷子和水性墨。這些不同導致西方活字印刷的技術較為復雜,且成本也較高,但印成的文字整齊劃一、墨跡均勻,版面效果較好;木刻印刷的特點則是簡便易行,且成本相當低廉,但是手工刻印的字形筆畫總有差別出入,也不易掌握水性墨跡的效果。當西式活字在19世紀初中期隨著西方勢力東來,在中國境內和木刻印刷交會后,就有人想到了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有沒有可能結合這兩種技術的好處為一呢?
最早企圖結合中西印刷術的人,是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在他以前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十分了解中西印刷術的不同,利瑪竇等人都曾在他們的書中談過,相較于西方的拼音文字,要鑄造幾萬個中文單字的金屬活字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在中國無法使用西方的活字印刷術。馬禮遜準備來華時,看過天主教傳教士的許多著作,他應該是知道這些情況的。但是,他于1807年來華后,面臨和天主教傳教士非常不同的困境,既無法進入內地,也不能公開傳教,便想出替代性的法子,到處散播他稱為“無聲傳教士”的印刷品向華人傳教,也因此,印刷出版成為鴉片戰爭前基督教在華的主要傳教工具。在馬禮遜的帶領下,初期的對華基督教傳教士嘗試過中西多種印刷方式,如木刻、石印、鑄版、西式和中式的活字等等,他還自費在澳門(后來遷到廣州)經營一家印刷所,使用石印和活字印刷,又進一步想結合中西印刷術為一。
1834年3月24日,馬禮遜從澳門寫信給在廣州的兒子馬儒翰(John R.Morrison),談論自己結合中西印刷術的想法和試驗:
希望你以中文金屬活字做個試驗,確認能否如同中國人的方式,以手工使用刷子和油墨刷印。……我急于知道是否可以不用歐洲印刷機來印刷中文。
我近來試過以中國刷子刷印,也相信這是相當可行的,隨附一份樣張給你。
我已訂了一些木板以備刻印,……如果你能為我準備一副鐵制組版架、一些楔子和一支木槌,就可以組成我旅行印刷用具的一部分,還需要帶一點印墨,其他如紙張、刷子在中國到處都有。
我幾次嘗試以油而非水和中國人的印墨混合,他們的水性墨很差。
馬禮遜手頭是有印刷機的,但是為了便于生產傳教印刷品,他試圖以中式刷子取代西式印刷機,并以西式油墨取代中式的水墨,再帶上其他必要的用品,形成隨身攜帶的一組印刷工具,準備前往各地隨時印刷散播。馬禮遜自認這種方式可行,也動手嘗試,還將樣張寄給馬儒翰,要兒子進一步試驗。
1834年4月1日,馬儒翰回覆父親,表示將依照吩咐進行嘗試。但是,那陣子馬儒翰正忙于其他事,在父子接下來的通信中,兩人都沒有再提到這件事,而馬禮遜隨即在四個月后的1834年8月1日病故,馬儒翰也收拾結束了自
家的印刷所,于是馬禮遜結合中西印刷術之舉不了了之。
在馬禮遜過世17年后的1851年,另一位基督教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也想到了結合中西印刷術的點子。理雅各原來并不喜歡印刷,鴉片戰爭前他主持馬來半島馬六甲布道站,曾埋怨布道站附設的印刷所只會浪費他的時間,他甚至將全部西式印刷機具都送給新加坡布道站。鴉片戰爭后他轉去香港主持倫敦傳教會的當地布道站“英華書院”,因為自己接連有著作要出版,他改變了對印刷的態度,而積極主動地管理布道站附設的印刷所。
英華書院的印刷所經營的是西式印刷,并且自行鑄造生產西式的中文活字。但是,理雅各在1851年4月22日寫給倫敦會秘書的信中,大談自己的新主意,說是已經向倫敦的供應商訂購一打毛刷,準備用來取代印刷機,以毛刷和中國墨水刷印金屬活字組版。理雅各認為這將大幅度降低印刷的成本,估計一本170頁的書印5000本,西式印刷的成本約275元,改用毛刷和中國墨水后,只收費200元卻仍有利潤等等。
理雅各的目的和方法不同于他的前輩馬禮遜。馬禮遜是企圖四處印刷散播傳教書刊以逃避中國官府的追查,理雅各則純粹考慮經營成本的損益。在方法上,兩人都想以輕便的刷子取代笨重的印刷機,但馬禮遜寧可使用西式油墨,而理雅各則要改用中國墨水。
理雅各沒有后續報告自己揉合中西印刷術的結果,另一位也是倫敦會的傳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卻替他說了。1852年2月23日,合信寫信給倫敦會秘書討論印刷,其中提到了理雅各的試驗,說是理雅各在幾個月前進行以毛刷和中國墨水刷印金屬活字的實驗,由一名中國印工嘗試了兩三天,效果很差而歸于失敗,原因有三:第一,易于流動的水性墨充滿在活字表面;第二,左右來回的毛刷動搖了排列整齊的活字;第三,粗短的刷毛損害了活字上細致的筆畫。合信表示,由此看來印刷機還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理雅各得到了中西印刷術難以結合兼用的教訓,沒想到13年后居然有機會以自己的經驗指點有著同樣想象的中國人。1864年2月24日,他寫信告訴倫敦會秘書關于印刷所的事務,提到了廣東巡撫的一名兒子到香港參訪英華書院附設的印刷所,并在詳細考察了三四天后購買了一批活字,表示將用于印刷巡撫衙門的告示等等。理雅各提醒對方,必須同時配備一部印刷機才行。巡撫的兒子卻認為以中國刷子和墨水即可刷印活字。理雅各告訴倫敦會秘書,對方必然會大失所望,又盼望這項預期中的挫折不致于讓對方打消以西式活字取代木刻的計劃。
理雅各并沒有指出那位廣東巡撫的姓名,但郭嵩燾從1863至1866年正在廣東巡撫任上,理雅各說的應該就是他了。郭嵩燾早先于1856年參觀英華書院在上海的兄弟印刷所“墨海書館”,也在日記中詳細描述墨海印刷機的構造與運轉,因此他對于西式印刷多少有些了解,而他三個兒子中的一位的香港之行也很可能是奉他之命。但何以只買活字而舍印刷機不顧,這些活字是否真用于印刷衙門公告,其結果又是否如理雅各預料的那樣讓郭嵩燾的兒子大失所望,都還有待查考。后來郭嵩燾出使英國期間,曾經參觀《泰晤士報》的印刷所和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印刷所,也分別記下了兩處的工作詳情,不知當時他是否還記得十二三年前自己或兒子想要結合中西印刷術的往事?
中西印刷不僅技術不同,經營形態也隨之大有差異。中國的木刻印刷成本較低,而且印完后刻板可以收藏,需要時取出再刷即可,因此不需多印,以免積壓成本和多占倉儲空間。而西方活字印刷成本原已較高,一書印完后通常即拆版將活字歸位,以便重復使用而節省成本,一書若要再版即需重新再做檢字、排版、校對、付印與裝訂等工序,所以通常印量較大,以降低平均單位成本和售價,并減少再版的麻煩。只有經典和暢銷書才會保留活字版,因為這類書的內容難得更動,而且會一再重印供應市場的需要。以上這些差異在這兩種印刷術于中國交會的初期,使得一些不明就里的中國人產生了誤會。
鴉片戰爭結束后,美國長老傳教會于1844年在澳門建立了一家印刷所“華英校書房”,1845年遷往寧波,改名為“華花圣經書房”,以西法鑄造的中文活字排印傳教出版品。由于大小和字形劃一,又使用油墨,印成的版面整齊精潔,傳教士表示書房的產品經常獲得當地官員和文人的贊許。
1846年4月間,一樁特別的生意上門了。當地一位喜愛華花圣經書房中文活字的張姓官員(傳教士沒有說明這位官員的名字與職位),帶來一種中國史書的抄本,希望傳教士以活字為他印刷50部。華花圣經書房經常為外國人印書或文件,這卻是第一次有中國人要求代印,于是傳教士在1846年4月25日的布道站會議中討論本案。
贊成代印的意見認為,此舉可增進華花圣經書房及其活字在中國人當中的知名度,同時書房只印過傳教圖書,代印此部中國史書有助于測試書房活字的完備程度,而且此舉不致妨礙傳教圖書的印刷,因為書房存書尚多,一時也沒有重要待印的書。
反對代印的意見則認為,此項代印根本不屬于傳教工作的范圍,何況此書內容有許多中國人的傳說寓言,代印將有可能被人視為傳教士贊同這些傳說寓言。而且此書篇幅不小,代印工期約需8個月之久,其間若有重要傳教圖書待印將造成困難。
傳教士討論后鄭重其事地進行記名投票,出席的5人中,贊成代印者4人,反對者只有1人,于是通過決議:只要張姓官員愿意付出合理代價,即為他代印。傳教士隨即將代印的決定和價錢通知張姓官員,不料卻從此沒了下文。一個月過后,傳教士婁理華(Walter M.Lowrie)于1846年5月30日寫回美國的信中表示,張姓官員不會再要書房代印了,因為他盡管喜愛書房的活字,但一本書以西式活字只印50部,單位成本之高嚇阻了他付印的意愿。
張姓官員肯定是從自己習以為常的木刻板印的觀念設想,認為成本應當不會太高,何況只印50部而已。他不知道西式活字印刷的成本較高,印量通常要大,才能降低單位成本。例如同一年(1846)華花圣經書房代印英國駐寧波領事羅伯聃(Robert Thom)的《正音撮要》一書,篇幅186頁,前后花了9個月時間印成500部,收費259.75元,單位成本是每部0.5元稍多。如果羅伯聃也和張姓官員一樣只印50部,則每部成本即使不至于正好高達10倍,也會是接近的了。可惜的是,傳教士的信件并沒有寫出為張姓官員代印的預定價錢。
從馬禮遜、理雅各、郭嵩燾之子到張姓官員,他們身處中西印刷術交會的初期,各自想象結合兩種印刷術的可能性。在這四個人以外,應該還有更多的人曾有類似的念頭和行動,例如1873年12月13日上海《申報》的頭版刊登社論“鉛字印書宜用機器論”:
頃聞蘇杭等處,來申購買鉛字者,接踵而至,但購買印書機器者,未聞有人。不知鉛字集成之板,若無機器,僅用人工,諸多不便。……既不惜鉛字之費,萬勿惜機器之貲,是本館所厚望于購買鉛字諸君也。
既然說買活字者多,而沒有人買印刷機,這顯示在1870年代的中國,有些印刷業者確是中西混用,以刷子刷印鑄造的中文金屬活字。刷子當然并非絕對不能用于刷印西式活字,只是效果和印刷機無法相提并論罷了,對于一向習慣于西式印刷效果的馬禮遜和理雅各等西方人而言,這是他們難以接受的,所以一試即罷。但是,19世紀初中期沒見過西式印刷或見得不多的中國人,無從比較也不會計較刷子和印刷機的不同效果,他們見到的是以刷子取代印刷機的簡便和經濟。何況中國傳統的活字排印本來就是使用刷子的,因此《申報》社論所說買活字而不買印刷機的情形其實并不離譜,而是中西印刷術交會初期混用雙方工具的一種過渡現象。
隨著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西式印刷術在中國日漸流行,進口的印刷機日益增多,后來又有自制的國產印刷機,西方印刷術終于超越并進一步淘汰了傳統的木刻印刷,也不會還有人想要以刷子來取代印刷機了。
“紙引未來”是造紙印刷包裝產業鏈B2B平臺,集行業資訊、行情分析、在線交易、集中采購、競拍、倉儲物流、供應鏈金融為一體的產業鏈服務平臺,PC+WAP+微信公眾號+APP全技術支持。






















 紙友
紙友
 行情
行情
 訂單
訂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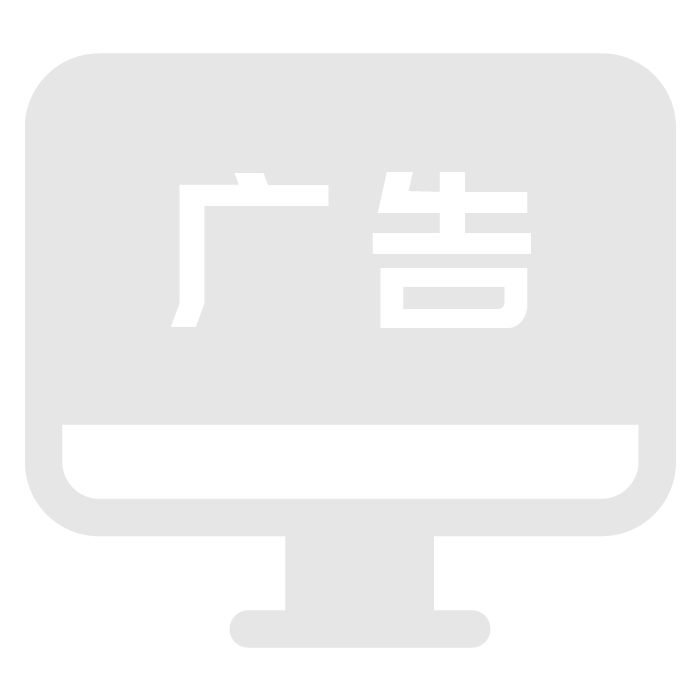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找貨
找貨
 簽到
簽到

 關注
關注
 客服
客服 TOP
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