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媒體出版行業中,充滿油墨芬芳的印刷總是長盛不衰。特別是在大學校園里,總是流傳著打印店老板的各種神奇傳說。
比如在北京,在任何一個大學周圍或者商務樓群的邊緣地帶,只要有幾棟“底商”的租價極其便宜的老式居民樓、幾排在拆遷的傳言中惴惴不安的小平房,甚至幾間用石棉瓦、白鐵皮搭起來的違章小窩棚,你都會看見一些招魂幡一樣神出鬼沒的簡陋招貼,上書“復印5分(雙面)、打印1角,量大從優”,在招貼附近,總會有那么一群老少混雜、拖家帶口的人在一個狹小的室內空間里圍著幾臺破舊的復印機、二手電腦、打印機忙得暈頭轉向,時不時可以聽見他們用同一種深奧得即使強行轉換到普通話的音軌上來也難以理解的方言相互催促、抱怨、嬉笑怒罵,一邊用粗糙的雙手復印、分揀、裝訂著跟他們的生活毫不相干的千奇百怪、包羅萬象的文字,一邊在相互之間頻繁的方言交談中傳遞著他們真正的生活:今晚誰做飯?是吃土豆還是吃豆腐?鄰街三舅的復印店里有人從老家帶了一包臘魚,派誰去取?
這就是湖南婁底市新化縣的復印打印軍團在北京開的三步一哨、五步一崗的復印打印店。不僅在北京,在全國上下都是如此。據統計,新化縣輸送到祖國各地的打印復印軍團占據了全中國打印復印市場份額的85%,而如此強悍的市場份額完全是靠一個個10平方米不到的逼仄、破舊的小門面壘出來的。
據說,這一軍團的形成純屬偶然:在上個世紀80年代,新化縣有一部分村民因為從事打印機、復印機的維修攢到了第一筆原始積累,后來有一天突然發現,機器不僅是可以拿來修,修完了還可以讓它雞生蛋、蛋生雞。于是一些新化人開始對準日益崛起的打印復印市場一陣猛攻,很快就以家族、鄰里、同鄉的傾巢出動之勢磕下了一條不易發覺的生財之道。在新化的一些村鎮里,90%的人都以馱著自家維修或組裝的二手打印機、復印機轉戰大江南北黃河內外為生,小孩們拼音都還沒學會、加減乘除都還沒弄明白,就已經學會了把復印機拆來裝去當巨型的變形金剛玩。這一軍團席卷文印市場的直接后果就是,凡有新化人出沒的地方,復印打印的價格一律低得令人咋舌,人們趨之若鶩,磚頭般厚重的書籍頃刻之間可以擁有無數廉價的副本,版權躲在法律條文的背后抹著苦澀的小淚珠。
我家附近就有這么一家新化人,其謀生之艱辛與頑強堪與“建青”媲美。他們先是在小區門口的一間平房里開店,不久,該平房被認定為違建,一夜之間夷為瓦礫。僅僅過了一天,他們又扛著機器跑到附近一家成人用品店,借店面里一塊5平方米不到的難以利用的犄角繼續做生意。大約是常去復印、打印的學生妹們羞于走進櫥窗里的樣品極度詭異的成人用品店,搬到這里后生意極其蕭條。一家之主一咬牙,又把機器扛到了交通干道上一個公共廁所狹小的潔具間里,頂著不便言及的氣味繼續為莘莘學子服務。
我一直也沒有弄清這家人到底有多少親戚在店面里從業。耳聾眼花的老者、染著一頭粵式碎發手臂上刻著粗大的“忍”字的蠱惑青年、吸溜著鼻涕滿地亂爬的小崽都曾在店里演繹他們的“復印人生”,但核心人員總是作為一家之主的一個吊嗓男和兩個頗顯勞動之壯美的女子。這兩個長得幾乎一模一樣的女子可能有一個是吊嗓男的“堂客”,另一個是他的小姨子,可是我去了這么多次,最終也還是沒有分清哪個是老板娘。


























 紙友
紙友
 行情
行情
 訂單
訂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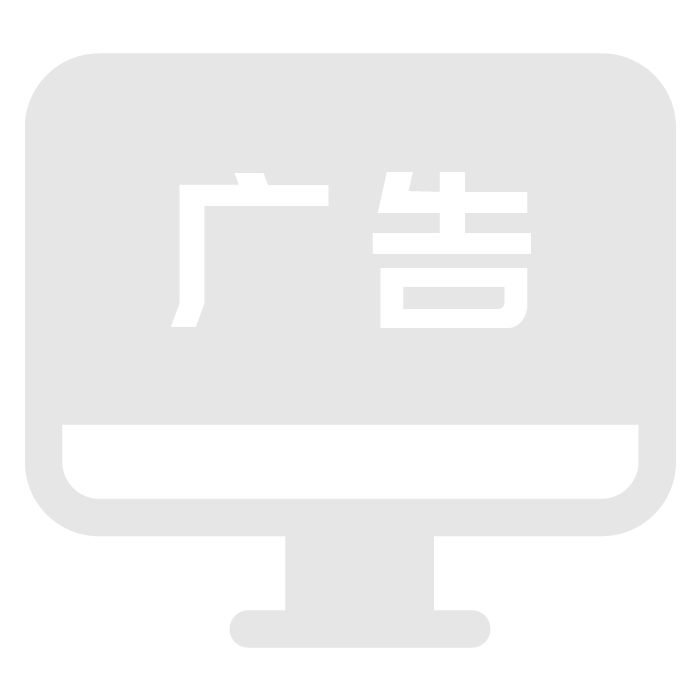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我要
我要
 簽到
簽到

 關注
關注
 客服
客服 TOP
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