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安徽師范大學教授黎澤潮《〈因話錄〉校箋》抄襲事件引起學界嘩然。人們在譴責抄襲者學術失范的同時,也把目光對準了出版社:為何一部錯誤頻出的書能夠順利出版?出版古籍類圖書,編輯、出版社是否應該具備古籍出版的專業資質?還有學者呼吁,古籍整理專業性較強,相關部門應當制定出臺古籍整理出版的規范,一方面便于編輯、出版社在實際工作中操作執行,另一方面也便于讀者判斷一部古籍整理著作的水準。
從兩家半到遍地開花 古籍出版繁榮背后有隱憂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內專業從事古籍整理的出版社有“兩家半”之說。“兩家”是指北京的中華書局和上海的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即如今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半家”則是指人民文學出版社,因其只有古典文學部從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出版社進入古籍出版領域。截至2014年,中國出版協會古籍出版工作委員會的理事單位已增至35家。實際上,從事古籍出版的出版社,遠不止這35家。
近年來,隨著人們對傳統文化的重視,不少非古籍社將業務拓展到面向大眾的普及型古籍出版物,有的還將古籍包裝成豪華的禮品書推向市場。而一些古籍社的情況恰好相反,由于學術類古籍讀者面較小,利潤有限,這些出版社出版的古籍圖書數量不斷下降,轉而更多地出版教材教輔。
“有人認為,古籍屬于公版書,出版社沒有稿費成本,利潤空間很大。其實,規范的古籍整理是一項繁難的學術工作,為整理者支付的稿費成本是比較高的。”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說,有些涌入古籍出版領域的出版機構,其實并不具備古籍編輯出版的能力。
“現在有人提出古籍出版準入制度,讓不具備資質的出版社退出古籍出版領域,我是很糾結的。”雖然身處中國最老牌的古籍社,但顧青并不認為只有古籍社才能出版古籍,“把古籍整理交給具備編輯能力的出版社,避免質量低劣的古籍整理圖書出現在市場上,當然是一件好事,但不能因噎廢食。把所有古籍集中到幾家出版社出版,是不現實的,畢竟古籍社沒有那么大的編輯力量,而且也不利于文化繁榮。從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的角度來說,應該有更多人參與到這項事業中,把具有資料價值、文獻價值的古籍進行出版、傳播。”
在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劉石看來,新中國成立之后,各出版社的出版領域曾經有一定的分工,像商務印書館以出版辭書、譯著為主,中華書局主要出版古籍、傳統文化類圖書,此外還有文藝社、科技社等專業出版社。但在如今市場化的條件下,只有通過市場優勝劣汰,讓讀者的購買選擇把那些圖書質量差、不符合學術要求的出版社逐漸淘汰出古籍出版領域。
顧青建議不具備古籍出版能力的出版社,可以采取與古籍社合作的方式,將古籍整理資源和策劃、營銷資源結合起來,共同推進古籍出版。
從乾嘉學派到現代學術 古籍整理需要新規范
糾結于古籍出版準入的顧青,對于支持對古籍整理出版進行規范的態度卻十分鮮明。事實上,中華書局早在幾年前就已經編寫出《古籍整理規范手冊(征求意見稿)》。
“現在學術界越來越強調學術規范,但從西方借鑒而來的學術規范,在中國傳統學術研究中并不一定十分合用。在古籍整理領域,清代乾嘉學者通過長期實踐已經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學術規范。然而,今天也有古人沒有遇到過的問題,比如新式標點,比如影印。”劉石同樣認為,推出古籍整理出版規范非常必要。
從20世紀90年代起,中華書局編審程毅中、許逸民等古籍整理專家就開始陸續撰寫《古籍標點釋例》《古籍校勘釋例》《古籍注釋釋例》《古籍今譯釋例》《古籍影印釋例》等系列文章,以舉例的方式,對標點、校勘、注釋、今譯、影印等古籍整理出版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工作進行了總結歸納。《古籍整理規范手冊(征求意見稿)》也將這些文章收錄其中。然而,在實際出版過程中,不按規范操作的現象比比皆是。
“我們現在大量推出的古籍影印本,在體例上駁雜混亂、各行其是,缺乏一種統一的合乎學術要求的影印規范。這種體例駁雜的影印本,既不可能為保存古籍版本提供更多的助益,也不可能成為學術研究的羽翼。”這是許逸民針對古籍影印出版亂象的批評。許逸民說,規范的古籍影印應該具有諸多條件,如,所采用的底本具有一定學術價值或文物價值,撰寫足以反映當代學術研究水平的序文,制定新的目錄或索引。而很多影印古籍沒有做多少整理研究和編輯加工的工作,就草率出版發行了。
顧青坦言,某些具體環節應該如何規范,并非沒有爭論。比如,有些古籍在“文革”中遭到破壞,被踩上了腳印,“有人認為腳印出現在古籍上,很不美觀,而且影響閱讀,主張在影印時通過技術手段把腳印修下去;有人則認為腳印是留存在古籍上的一種信息,應當保留”。顧青表示,可以先把學界、出版界的共識形成一個統一的規范,至于存在爭議的地方可以留待未來慢慢解決。
“在信息時代,人人都可以在網絡上發表自己的作品,有人因此質疑編輯存在的必要性。其實,在眾多參差不齊的書稿中遴選出優秀書稿,并將其編輯成符合規范的出版物,是編輯的重要職責。”顧青說,在信息時代,編輯的價值將更加得到彰顯。






















 紙友
紙友
 行情
行情
 訂單
訂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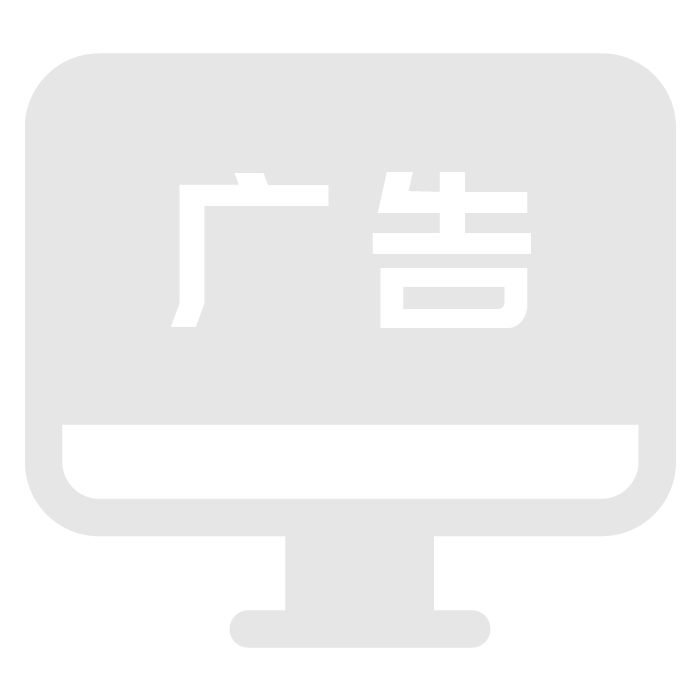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找貨
找貨
 簽到
簽到

 關注
關注
 客服
客服 TOP
TOP

